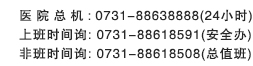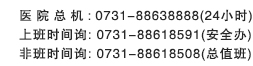在古城长沙,他拿下了国际医学界瞩目的异种移植科研成果,给数以万计终生“臣服”于胰岛素的糖尿病人带去了新的希望;他与同道共同参与制定的全球异种移植临床研究规范《长沙宣言》,为国际异种移植医学的发展开辟了健康的“航道”,也使得国际医学临床规范首次被烙上中国印。作为我国猪胰岛细胞移植治疗糖尿病的拓荒者,10多年来,他在无数期盼的目光中负重前行。
2008年11月,湖南长沙。由世界卫生组织(WHO)和中国卫生部主持召开的全球异种移植临床研究规范国际研讨会如期在此召开。一位小个子中年人——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放射科主任王维教授在台上就“异种胰岛移植在中国”论题侃侃而谈,台下静静聆听的,是联合国世卫组织官员和国际移植界顶尖“大腕”。
研讨会上,来自全球24个国家和地区的顶级专家,对王维在异种胰岛细胞移植治疗糖尿病方面实现的重大突破不乏赞美之词,同时,也对他为规范异种移植行业标准作出的成绩给予肯定。由王维团队起草、卫生部组织专家审定通过的《中国异种移植临床研究规范(草案)》,被当做了“国际异种移植临床研究规范”的重要蓝本。更让王维激动的是,这次研讨会通过了针对WHO成员国异种移植临床规范的纲领性文件《长沙宣言》,国际医学临床规范第一次被烙上中国印。
卡尔教授的“最高奖励”
王维和国际医坛“巨匠”卡尔教授的跨国友谊被“圈内人”传为佳话。
2005年5月,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国际学术年会上,王维异种胰岛移植治疗Ⅰ型糖尿病的研究报告引起了轰动。
8月,王维收到了一封特殊的来信——发件人是名叫卡尔•格罗斯的英国人。他在信里称赞王维做了“先驱性的工作”,并对自己因故没能参加5月的会议表示遗憾,希望能在当年于欧洲和巴基斯坦召开的两个国际学术会议上见到王维。王维婉拒了他,“这两个地方我都不能去。10月在中国有个会,如果您来,我们欢迎。”
没想到,年逾七旬的卡尔教授果然来长沙了。与会的一位国内著名科学家告诉王维,这人可了不起,他是国际异种移植先驱,国际异种移植协会第一任主席,原诺贝尔生理医学奖评委会主席。“有眼不识泰山”的王维暗想糟了,没坐主席台甚至连正式代表都不是的卡尔对此却毫不介意,和王维相谈甚欢。这一次相见让他们成了忘年交。第二年春天,卡尔专程来长沙考察王维的实验室,并应邀成为湘雅三医院的客座教授。
“卡尔教授对我的帮助非常大。从他那里,我了解到海量的、最前沿的国际最新信息,他为科学献身的精神也让我感动。”在王维看来,这位大师还是个“性情中人”,“我们做猴子实验时,卡尔教授担心我们做不成功。后来看到实验做得相当漂亮,他高兴得在实验室大喊‘请客’,请我和几个年轻人到肯德基吃冰淇淋,这可是他的‘最高奖励’了。”
正是在这种国际交往中,王维开阔了视野,也赢得了和很多医学大家跨国合作的机会。
“科学家之间的交往,主要看你在这个领域的成就,你有成果,人家就尊重你。”王维给记者讲了一件趣事:2007年,卡尔教授和他一起到美国访问,专程到匹兹堡大学器官移植研究所看望了卡尔教授的老师——80多岁的Starzl教授,全球第一例肝移植就是他做的。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这位骄傲的“祖师爷”正眼都没瞧他,边和他握手,边和别人说着话。卡尔把他在中国的工作进行了介绍,老人立即对他刮目相看,主动提出要听他第二天在匹兹堡大学Starzl研究中心的报告。报告刚一讲完,老人迫不及待地扑过来,来了个典型的“美国式拥抱”,还要和他合影,并开着自己的小车,邀请他和卡尔到家里吃饭。饭后,他们又一起兴致勃勃地去看喜剧大片。在电影院里,全球异种移植领域的三代学者,时不时爆发出孩童般顽皮的大笑……
很多人都纳闷:这样一位其貌不扬的矮个子学者,何以能在一所只有十多年发展历程的年轻医院引领一个普普通通的辅助科室,一举拿下各国科学家梦寐以求的研究成果,得到医学泰斗的青睐和全球同行的尊重?
带着同样的疑惑,记者寻访王维“梦开始的地方”,试图找到他通向成功的“密码”。
和初中生一起练英语
“我是我们家第三代湘雅人。”王维以此为荣。他的外祖父和父母都是湘雅毕业生。有着湘雅情结的他从小就做起了医生梦,然而求学之路并不顺利。
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王维正在长沙一家工厂当电工。为了心中的大学梦,他和几个好友宝贝似的共用着借来的旧课本复习。一个多月后,王维忐忑不安地走进考场。成绩出来后,上了重点线,却没被录取,据说是因为他个子矮。第二年,他又考,克服重重困难,终于成为了一所医学院校的大学生。虽然学校没什么名气,但“有书读就很满足了”,王维没时间去抱怨,而是全身心投入学习中。
1985年,当了3年放射科医生的他深感自己学得不够,于是报考了河南某医学院生理专业硕士研究生,尽管总分和生理学专业都考第一,但被校方以“专业隔得太远”而拒之门外。这次失利让王维一两个星期都“不太爽”。但他迅速调整状态,来年考上了湖南医科大学附属湘雅医院王焕申教授的放射专业硕士研究生,终于梦圆湘雅。
“王焕申老师一字一句给我们改报告,一个字写得不好,重写!”严谨的湘雅精神给了王维良好的熏陶:做事严谨扎实,对待病人认真负责,善于团结协作。3年后,他成为湘雅医院放射科医师,因为勤奋,他的阅片水平逐渐在省内赫赫有名,介入治疗也做得相当漂亮。2000年,他又开始攻读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医学遗传学,拿下了博士学位。
即便是成为了声名显赫的医学教授、博导,他仍学习不辍。为了攻下英语口语这一“短板”,他上起了夜校,旁边坐的常常就是一些上着初中的小姑娘。“我和初中生能有多少共同话题啊,没话找话,就从最简单的句子开始练。”夜校老师于是夸他“特别认真,是个好学生”。晚上10时下课,他得坐40分钟的公交车回家,“耽误一点时间就没车了。”在他家墙上,则贴满了写着英语单词的小纸条。如此苦练,他的口语提高很快,日后在频繁的国际交往中应用起来也游刃有余。
学生、同事都对王维佩服得五体投地,说他有超常天赋。王维却一语道破玄机:哪有什么诀窍,不过是别人玩时我在看书罢了。
“办法总比困难多”
1992年,一个平常的下午,上级领导找王维谈话,要他到卫生部和湖南省重点投资新建的湖南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前身)组建放射科,毫无准备的他第一反应是“怎么会是我?”,当时,他还只是主治医生。
几天后,32岁的王维走马上任,担起了放射科主任。他发现“困难远比想象大”:医院边建设边开诊,新门诊大楼孤零零立在荒野,不通公交车,一下雨就满地泥泞,上班得穿套鞋。放射科就两间房,两名医生,加上其他医护、工作人员也不过六七个人。王维和同事每人轮班连续工作24小时。
科室的筹建,一切得从头开始。他们从国外买来了二手设备,安装调试全得自己来,没有说明书可供参考,甚至一些小配件也找不着。 “我们坚信‘办法总比困难多’。为了配一台仪器上的螺栓,跑了几十里地,找遍长沙的五金店,最后在电力局发现一种电杆螺栓,回来一试正合适,几个人都乐坏了。”说起当年事,放射科的“元老”周技师记忆犹新。没配件就自己做,好在从小爱好物理又当过电工的王维动手能力很强。
经过一番艰苦创业,王维终于不负重托把医院放射科建起来了,并带领这个科室一步步发展壮大。王维本人的业务水平也与日俱增。
“再侧过来一点。”这已经是王维第三次要病人调整体位了。这是位受外伤的老太太,前两个角度拍出来的片子下级医生都没有发现问题,王维还要坚持再做一次。第三次结果出来了,王维惊出一身冷汗:一侧肋骨全断了!类似的疑难杂症难逃王维的“鹰眼”。1987年,他开始从事放射介入的工作,是湖南省少数几个最早开展放射介入疗法的人之一,临床水平令同行佩服。
王维还发起了对门脉高压、肿瘤治疗、消化道出血和帕金森病等的冲击。他采用分子影像学方法研究中枢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报告基因影像学诊断机制,先后赢得了“CT引导脑内植入腺相关病毒载体(AAV)表达酪氨酸羟化酶基因特性的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门脉高压食管静脉曲张治疗对策研究”和“门脉高压上消化道出血预测及非手术治疗的研究”两个卫生部临床重点项目资助,并获得1项国家专利。在全国放射学优秀论文评选中,王维连续荣获第一届、第二届“刘玉清优秀论文奖”。
2004年6月27日,被称为分子影像学“发展里程碑”的我国首届分子影像学学术大会在长沙召开。会议的发起者、组织者和组委会主席正是王维。他作的主题发言“细胞生物学与细胞移植的发展催生了我国的分子影像学”赢得阵阵喝彩。
著名放射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刘玉清称赞王维是“率先在中国开展分子影像学研究的主要学者之一,他所做的工作具有国际先进和国内领先水平”。
10万元起家搞科研
随着介入治疗临床实践经验的积累,王维在大量文献的阅读中受到启发:能否采用介入的方法,用人以外的动物胰岛细胞移植治疗糖尿病。这个念头令他非常兴奋,并为此开始积极准备。
糖尿病被WHO列为世界三大难症之一,胰岛细胞移植是目前公认的根治糖尿病最佳手段之一,但同种移植的人源供体连1%的病人的需要都不能满足。临床异种移植三四十年前起就备受关注,发达国家先后投入近十亿美元搞研发,却收效甚微。
1997年,王维在简陋实验室里开始着手猪胰岛细胞移植治疗的研究。之所以选定猪胰岛细胞,他解释说,“猪胰岛素和人胰岛素结构极相似,仅差一个氨基酸。临床也证实,长期使用猪胰岛素治疗人糖尿病有效。且猪的繁殖期短,只有19天,胰岛细胞容易获得。再者,猪与人共同生活数千年,相互间不存在难以控制的人畜共患疾病,不存在伦理问题。”
但他当时听到的却是一片质疑声。好在有医院“撑腰”。“医院在创院之初非常艰难,还挤出10万元科研经费给我们!”提起医院的“雪中送炭”和几任院领导的鼎力支持,王维很是感动。靠这10万元起家,王维开始了艰难的异种移植之旅。
然而仅靠这10万元显然不够,经费短缺是他们在研究之初遇到的最大难题。他们不得不精打细算,有时甚至自掏腰包做实验。1998年,王维拿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经肝动脉肝内移植异种生物人工胰腺的实验研究”。那天放下电话,王维好久还沉浸在兴奋之中——这是湖南放射专业拿到的第一个国字号课题。2002年他又申报了一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腺相关病毒载体(AAV)转导猪胰岛细胞表达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相关抗原4抗体(CTLA4Ig)肝内阻断异种宿主T淋巴细胞活化研究”。在这两项国家课题30万元的资助下,研究得以顺利开展。短短几年时间,他的实验室已经拥有了500多万元的先进装备。
有句话他常挂在嘴边:做事业,有条件好好做,没条件创造条件做,不等不靠,不怨天尤人,多动脑筋想办法。国内在异种移植方面可供借鉴的经验一片空白,为此,王维跑遍了长沙的图书馆才好不容易在国外杂志上发现有零星的介绍。
控制动物病毒传播风险,是异种移植中极其关键的一环。体内含有PERV-C 病毒的猪,可能存在发生猪源性病毒感染的风险。为寻找最适宜的供体猪种源,王维北上青藏高原,南下海南岛,到十几个省区的偏远乡村筛查了几十类猪源。为此,他曾在青海一家保种场,跳进了臭味难闻的猪圈提取30多头猪的血液标本;也曾直奔海南岛腹地——黎族聚居的霸王岭,深入农户挨家挨户寻访纯正山地猪。几年内,他们行程数万里,采集并研究了11个我国独有的纯种猪种,从其中筛选出最适合移植用的猪源,并在湖南省建立了两个初具规模的猪源基地。
一切就绪后,王维带领自己的团队开始实验室研究:从猪体内取出胰岛细胞,通过体外“消化”、“纯化”等程序加工,制出活胰岛细胞悬液,然后将其注入受体肝脏中。但要让猪胰岛细胞在人体内存活下来,还要消除免疫排斥反应。由于他们的“消化”、“纯化”做得很好,又有好的移植方法,加上部位和用药准确,从而有效地控制了免疫排斥反应。
经过卫生部批准,研究很快从实验室研究走向临床研究。王维采用自主开发的微创介入方法和自行研究的针对异种胰岛细胞移植的抗免疫排斥治疗方案,先后为22位Ⅰ型糖尿病患者进行猪胰岛细胞移植治疗,其中20例全部有效或显效,病人基本摆脱了疾病的折磨。经过5年追踪,所检测病例均没有猪源性病毒感染征象。特别令人鼓舞的是,他对两位糖尿病人分别进行重复(两次)移植和新移植方案的研究,其中一位病人可短期脱离胰岛素,一位病人获得显著改善。有位病人常发生酮性酸中毒,生活难以自理,只能依赖胰岛素住院治疗,经异种胰岛细胞移植治疗后,胰岛素用量减少30%,病情明显好转,不仅恢复了正常生活,还能外出打工。
2004年6月,卫生部专家组对课题进行了全面评审,一致确认王维团队在国内外率先创用经肝动脉进行肝内移植猪胰岛细胞,在临床治疗中取得了好的疗效,达到了国际先进、国内领先水平。
在用猪胰岛细胞治疗糖尿病取得了突破后,王维又花极大的精力完成了猪胰岛移植到恒河猴的实验。很多人不理解:猪胰岛临床移植都做成功了,再做猴子实验有无意义?更何况灵长类动物移植实验设备及人员要求高,困难重重,在美国也只有极少的实验室可做。
王维认为,猪胰岛移植的初步临床研究虽然已初显成效,但进一步研究的有些参数只能在灵长类动物的实验中才能取得,缺乏它,课题就有未知的死角。他带领课题组克服诸多困难,在国内率先完成一次性大规模的猴群实验,完成了在恒河猴糖尿病模型新生猪胰岛肝内移植技术和抗免疫排斥治疗方案的研究,取得一批宝贵的实验参数,确保了异种移植的安全可靠。
他坚信,往前走一步,哪怕只是一小步,离梦想的距离就更近一步。
“异种移植不但具有重大的医学科研创新性,还具极大商机。这样一个重大课题,一定要符合伦理基本原则,如果没有统一严格的国际规范,是很危险的,也有悖科研的初衷。”科学家的良知和责任感时时提醒着王维。如何规范异种胰岛研究成为他的新使命。受卫生部委托,王维团队提出的《中国异种移植临床研究规范草案》于2008年10月顺利通过卫生部专家组审定。11月21日,王维和他的同道们共同参与制定的全球异种移植纲领性文件《长沙宣言》应运而生,为国际异种移植医学的发展开辟了健康的“航道”。
近10年来,王维的身影不断出现在国际讲坛。全球医学界的目光也开始聚焦于这个神奇的“东方小个子”。
“不能一味迷信文献”
“严谨的湘雅精神是老一辈湘雅人给我们最大的财富,我们有责任一直传承下去。”王维经常告诫学生,做学问绝不能有半点弄虚作假,如果对哪里有怀疑,要千方百计确定,哪怕多做几次实验,推迟发论文。
王维的学生邢晓为对此感受极深。刚开始做实验时,他们扩增PERV片段长度和国外文献报道不一样,邢晓为很困惑。但导师王维毫不含糊:“不能一味迷信文献!但我们的东西也要保证有百分百的把握。重做实验!”3次实验下来,他们的数据都没错,王维果断决定:做基因测序! 结果也验证了他们的数据。邢晓为把这些原始数据附在论文后面,缜密的做法得到了《遗传》杂志社的高度肯定。论文仅19天就被正式接受了。“后来经国际基因BANK对比,我们的数据是完全可靠的。”
刘博士是王维第一个博士研究生,如今已成为王维的左膀右臂。从最开始搞核磁共振,到后来做胰岛移植,她都是“先锋”。刘博士称自己与导师相处有十多年,太了解他了,“他对学生相当严格,谁也别想蒙混过关,我读他的研究生就推迟了一年才毕业——因为课题没有做到尽善尽美。”尽管当时有些不理解,今天她却格外感激:“我们现在工作很顺利,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导师当时的高标准严要求,使我们的基础过得硬。”
王维习惯于把对学生的关心体现在严厉中,他教导学生“板凳宁坐十年冷”,搞科研一定要沉下去,再沉下去。他发起的研究生沙龙多年来雷打不动,每周星期四晚上7点半准时开始,一般两小时,有时要开4个多小时。会上大家可以畅所欲言,说各自课题的进展、困难和设想,或是看书心得,或者对别人的课题提出建议。王维幽默地说“没有读书的讲个故事也可以”。当然,迄今为止还没谁讲过故事,讨论热烈,效果非常好。年轻的学生讲求生活情趣,撞上圣诞节、情人节之类的日子,想和王维商量推迟一天开,但结果是“没门”!后来学生们谁也不敢再有“非分之想”了。
“科学是严肃的,科学家并不总是严肃的。”说此话的王维本身就是很好的例子。
“王教授歌唱得好,菜也做得好。”熟悉他的人都知道,生活中的王维其实多才多艺。他从小就爱锻炼,羽毛球、乒乓球、篮球,什么都喜欢玩两下子。他还喜欢跑步——为了有足够体力应付工作。从刚工作时组织野炊,到现在科里的年终Party,他都很活跃。
王维的办公室挂着一张照片,儿子举着“奥运火炬”——卡片做的模型,很可爱。“那是他的梦想。”说起儿子,王维的眼睛充满慈爱。和所有父亲一样,他对儿子看得很重,每周和儿子两次谈心,是他的必修功课。
■王维小传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主任医师,影像医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放射科主任、影像医学与核医学教研室主任,中南大学湖南省胚胎干细胞研究中心副主任,国家干细胞工程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介入放射学及分子影像学。在胰岛细胞肝内移植、移植免疫以及帕金森病基因治疗等方面多项研究成果达到国际先进和国内领先水平。近年来作为课题负责人获得3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3项卫生部临床重点项目、l项卫生部科研基金课题。近5年在国内外一流学术刊物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学术论著7部。